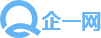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何为“大学之魂”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或者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
大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功能。
同时,大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人认为,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大还算不上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如果看一所大学在她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她的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大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在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汲取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头脑。这样他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为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了基础。而且,尽管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却更加重要。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遗传”则是大学对自身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又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大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一份宁静和清醒。
前些年有个说法,说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这些年大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为世风恶俗推波助澜。只有如此,大学才能排除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在稳定而宁静的环境中潜心钻研,学生也才能一心向学。此外,大学还应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上面讲了大学“保守”的一面,现在我们再谈谈她“创造”的一面。与坚守“精神围墙”同样重要的,是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不时地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人类的社会远非完美,总该有一批人来认真研究和批判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等于是放弃了大学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
然而,反省不仅仅是批判,更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更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大学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研究讨论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给出我们的回答。也许,有些问题看起来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但正是这些研究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去创造新的精神资源和思维方法,去丰富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或者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正是“坚守性”和“创造性”构成了“大学之魂”。
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
对当今的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大学还有第三个使命,那就是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使命。我并不认同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来划分大学的功能,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使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始于二战。那时候很多国家的政府给大学投入资源,希望她们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那时候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和破译密码的方法等,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大学就具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人们认识到科技知识能够转化成生产力。这时,大学就扩展了服务这一方面的功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就曾在《大学之用》一书中写道:“今日之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大学应当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那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我也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且必须的。大学服务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那么一大批辛勤钻研的学者。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的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者、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人才的培养机构,必须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并以此来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
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却开始反省,认为自己在服务这一头走得太远了。因为,当时的美国高校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大学在二战后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比如就有人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客观的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而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得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大学,人们就会在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国内近些年来不少关于大学的讨论,就带有类似的倾向。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大学已经堕落为“服务站”。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也曾经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旦政府、社会和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就只能为社会提供即兴式的服务,不仅质量不高,而且还会使大学过度政治化、社会化、市场化。
以上两种倾向性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具有镜鉴之义: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我国的大学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保持大学本身应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对当今的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相比“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存在的张力可能更大。
但这些“张力”往往又都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的大学要学会在以上种种张力中前行。
为理想而学习
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而言,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被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有些学生进校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大家都是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复旦大学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认真地来问一问自己:你到底为什么来复旦上大学呢?
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人是为了赚大钱,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当然也肯定有不少学生对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抱负,他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意识到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担负起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些答案都无可厚非,但关键要看哪些占了主导地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几种目的而求学是很不屑的。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大概也不会对纯粹因前几种理由来复旦上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眼光。我想告诫大家的是,如果你淡化了“为了谋生而求学”的目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一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从来不认为理想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更不同意将其等同于“不食人间烟火”。我一直认为,只有抱着理想主义的情怀,一个人才会认真地投入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重重危机,比如世界上现存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又如金融寡头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人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时,我们就更应该守护理想主义,为理想而学习。复旦是一所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而复旦的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大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复旦也应该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
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曾提到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一次有关其学习动机调查,就问了一个题目:你到哈佛上学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则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当20年后,人们对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当年受调查的这1520名学生中,有101人成了百万富翁,其中100人当时的选择就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当理想主义深藏于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会不断地支持他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并在其受到俗事纷扰的磨砺时,能够随时回归自己的内心,重新出发。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而言,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被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在面对挫折、面对死亡时,都可以泰然处之。因为有信仰,才能克服困难。
此外,作为一名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无论如何,只有你们自己才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体。恰如怀特海德所言,“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同样,你们也不是供父母随心捏成某个人的胶泥。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应当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无论你们的学习生活是苦不堪言,还是会其乐无穷,关键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再次引用怀特海德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而且,“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责任与理性
大学生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之后,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大学生的最大责任。
然而,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却常常可能让我们“心向往之”而“遥不可及”。正因此,除了为理想而学习,你们还应在当下就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去当志愿者,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然后学会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种种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现实。
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曾亲笔写就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而其在上海乃至在整个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日本侵华时,复旦学生组建了“学生义勇军”,还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承诺“保证抗日”。所以说,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复旦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鄄vice)。我把这个称之为“Sof3S”。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有知识、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是不可取的。我国“文革”时期的教训也很深刻,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那场浩劫,人性尽失,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金耀基先生曾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正常的社会应有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地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但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要“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只要不是“非常”时期,社会并不期待你们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大学生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之后,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大学生的最大责任。
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都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后来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且无可估价的回报,因为“通过它,我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而且,“通过与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我认为这些话很实在。因为你们,在座的同学们,尽管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较幼稚,但正因为这些幼稚,才成就了你们主动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因此,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培养你们良好的德行,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而学习、奋斗,也是作为学校管理者和教学者的我们,应当担负起的使命与责任。